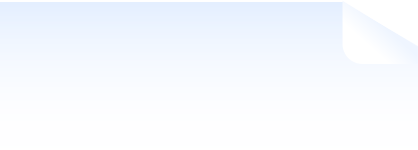韩 晗 | 红色工业遗产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机制与路径
摘要 红色工业遗产作为一种承载着媒介记忆的记忆场所,在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不但在内容与形式上具有统一性,而且在主体与客体上具有同一性。就传播机制而言,有回到历史现场的“凝视—沉浸”、形成物质感知的“抽象—具象”与阐释时代价值的“历史—现实”三种机制。从传播路径来看,则包括保护更新、IP赋能与社区参与三种,这又是由红色工业遗产时代性、创新性与人民性三个改造再利用的方向所决定的。在推进红色工业遗产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过程中,要避免同质化与庸俗化。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红色工业遗产;传播;记忆场所;媒介记忆
韩晗,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武汉大学景园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一、红色工业遗产的概念及其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党史,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工业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作为工农联盟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工业天然地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联系。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工人运动与工业生产工作,以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陈潭秋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活跃在工业生产一线,在安源煤矿、大冶铁矿与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等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苏区、边区与解放区等根据地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实现军事斗争与工业生产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如中央红军曾在瑞金开设印刷厂、兵工厂等企业,实行军需自给自足;新四军在苏北、皖南等地筹办大鸡烟厂、东海烟厂等多家工厂,八路军则在冀晋鲁豫边区开办被服厂、造纸厂,开辟出以工养战的局面;党中央在延安兴办利民毛纺厂、新华化工厂、振华造纸厂等工业企业,为本无工业基础的延安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成为党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
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而形成的红色工业遗产体系由是而生。它与革命文物有着密切的交集,具有无可取代的红色文化资源,其核心价值由党史价值所体现,在我国工业遗产乃至文化遗产体系当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从宣传教育的角度来说,它是“四史”的重要见证。
红色工业遗产体系庞大、数量巨大、意义重大。本文所言之红色工业遗产,既包括已纳入文保框架下的重要文物,也包括未纳入文保框架但却有重要价值的历史物证(如大量改革开放工业遗产)。从内涵上讲,它与革命文物类似,包含可移动与不可移动两个类属,其形成过程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息息相关。
(一)二者在内容与形式上具有统一性
与其他历史古迹相比,红色工业遗产多问世于近代以来,存世数量较多,而且,一些红色工业遗产至今仍承担或部分承担生产职能,因此所形成的媒介记忆也具有连贯性,甚至当中不少遗产本体完整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某种具体精神的发展沿革(如大庆油田与“铁人”精神),构成了重要的记忆场所。就此而言,红色工业遗产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构成了“形式—内容”的关系。
作为媒介记忆的载体,红色工业遗产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历史的痕迹与物证,天然地具有讲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相关故事的合法性,特别是将故事当中的细节以“百闻不如一见”的方式予以视觉呈现,展现媒介记忆,增强了传播效果的生动性。而且,红色工业遗产又是具有物质性的记忆场所与具有场景再造功能的文化景观,小到文博陈列、文化创意,大到城市更新,红色工业遗产都有深度参与的空间,并可以通过日常生活美学的渠道形成更广维度的场景传播。
举例而言,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苏区精神”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建军纲领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白手起家建设了苏区军工事业。但因当时特殊历史环境制约,苏区军工事业在对敌军事活动中隐蔽辗转,如最先曾在福建成立山塘兵工厂,后又在江西兴国创办官田兵工厂,1933年底迁至冈面,改名为中央兵工厂。因此,苏区兵工厂遗址多处于散乱甚至湮灭的状态。2011年,在中央有关部委、央企与江西省地方政府的积极努力下,中央兵工厂遗址建筑本体得到修复并整体迁建到了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政府旧址旁,与苏区印刷厂、铸币厂、无线电厂、被服厂等工厂旧址毗邻,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苏区红色工业遗产群,并开发了主题文创产品与文旅体验项目,年接待游客数百万人,“苏区精神”的传播也突破了先前以文艺作品与历史档案为主的局限,形成了依托记忆场所进行场景传播的新局面。
(二)二者在主体与客体上具有同一性
作为一种记忆场所,红色工业遗产为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了重要载体。从本质上讲,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符号,它根植于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写照。在自媒体时代,意识形态的传播既通过遗产本体对受众的传播来实现,也因受众在接受信息之后的再传播得到进一步普及。因此,红色工业遗产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主体与客体上具有同一性。
这里所言之场景呈现,即通过改造再利用红色工业遗产,从而实现媒介记忆的符号化转化,以提升其传播价值。改造再利用红色工业遗产,目的在于阐明其“红色”符号——即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符号的标出性(marking),使遗产本体从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景观转变为一个具有文化符号传播功能的历史场景。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而是形成了从可沟通性(communicating)、可塑性(plasticity)到可参与性(participation)的三级复合传播路径。作为传播主体的红色工业遗产本体与作为传播客体的受众,在记忆场所(主体)中实现了媒介记忆的交互传达。传播主体指的是“传播者”即传播观念的载体,它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承载观念的物体。在传播过程中,客体的观念既被主体塑造,同时也塑造主体,这种塑造通过不同个体受众的感知、体验与消费对遗产本体的客体再阐释——如通过自媒体形成SoLoMo的传播结构,进而构成主体与客体的双向可参与性,最终实现红色工业遗产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有效传播。
我们调研发现,目前国内大量红色工业遗产以建筑物、构筑物或建筑群、大型设备与遗址等形式表现,而改造目的又多为“一馆三区”(工业博物馆、工业主题街区、工业文旅园区或城市主题社区)为导向,当中大多数工业遗产都具备场景呈现功能,不少红色工业遗产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甚至成为“网红打卡地”。如梓潼“两弹城”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历史物证,并收录于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但因其较成功的文旅开发(包括全国唯一的“原子弹爆炸3D视频体验”),得到了游客特别是“旅游博主”在抖音、小红书、马蜂窝等自媒体平台的自拍、直播等“种草”式宣传推广,近年来成为了备受关注的“网红景点”,实现了“两弹一星”精神的二次传播,形成了遗产本体与具体精神在主客体上的同一性。
三、红色工业遗产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三条路径
作为一种不可再生文化资源,文化或技术史载体是工业遗产被公认的最大价值,也是工业考古学重点关注的对象。不少红色工业遗产尚未列入文保框架,一方面,这给红色工业遗产的保护留下法律上的空白地带,时常造成“应保未保”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这也赋予了红色工业遗产更为开阔的改造空间,使之尽可能地发挥其可塑性与可参与性价值。就目前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现状而言,大量得到妥善改造再利用的工业遗产,多是通过城市更新、文旅融合或文化再造等方式,将“一馆三区”作为改造目的,这也是目前国内工业遗产实现改造再利用的重要途径。但就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路径而言,红色工业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主要有三条传播路径:保护更新、IP赋能与社区参与,而这又是由时代性、创新性与人民性这三个红色工业遗产的改造再利用方向所决定的。
(一)“精神谱系+群众路线”:基于时代性的保护更新
与革命文物不同,大量红色工业遗产以历史建筑或构筑物的形式体现,部分尚处于使用期限范围内,而且多数遗产具有社区属性,属于曾经的大型国有企业旧址,是成规模的遗产群,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深度融入。对具有社区属性的红色工业遗产保护更新,需依据其时代性特征,打造“群众路线”的传播路径。
理论只有被群众接受,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传播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时偕行的发展之路。目前承担先进文化传播的物质媒介主要是革命文物,但革命文物目前存在着保护薄弱、挖掘不足、利用浅显等实际情况。而红色工业遗产凭借其可塑性特别是可参与性特征,在满足时代需求中当有更大作为。
因此,满足时代需求是红色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重要方向,它可以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遗产的全新面貌,进而在潜移默化中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实现“精神谱系+群众路线”的传播路径。以深圳华侨城创意产业园为例,该地曾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东部工业园”,一度聚集60多个工厂,时称“特区第一工业园”,被誉为“深圳特区建设的活化石”,属于改革开放初期重要的红色工业遗产。经历产业结构转型后,深圳市政府为适应经济发展与市民精神文化等时代新需求,与央企华侨城集团联手将其改造成主打特区文创特色的华侨城文化创意园,并开辟有关图片展厅,年接待访客逾百万人,一度成为自媒体上“吸粉”无数的“网红打卡地”与周边群众“微度假”的首选去处,成为传承“改革开放精神”的重要阵地。
此外,“群众路线”还应重视自媒体与大众媒介的推动作用。如梓潼“两弹城”提供给游客自拍、直播等对外宣传渠道,形成了较大社会反响。2021年3月,文物学者单霁翔应浙江卫视之邀,联合文艺名人,在湖北省黄石市拍摄“万里走单骑”系列节目,介绍黄石红色工业遗产与工人运动史。2021年7月,央视新闻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宣传中心等机构,制作“网红打卡地&工业遗产”节目,集中推出了一批红色工业遗产地。上述电视节目通过对红色工业遗产的宣传,生动传播了“苏区精神”“雷锋精神”与“铁人精神”等伟大精神,为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精神谱系+红色文创”:基于创新性的IP赋能
红色工业遗产之所以具有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在于红色工业遗产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从文化产业理论看,它具有智慧产权(即IP,Intellectual Property)特征,这是彰显文化遗产特征的核心符号。不言而喻,红色工业遗产的IP就是红色文化,即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中所形成的精神积淀。
近年来,随着文博文创的迅速发展,相关历史主题IP的文创可谓百花齐放,形成了以故宫文创、敦煌文创等为代表的文创体系,在文创产品开发上,也体现出了从实体产品向商业服务、虚拟产品过渡,从IP授权向IP转换的纵深转型。但红色文博文创却是我国文博文创领域的短板。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红色文化的IP化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舆论与政治风险,这使得一些文博机构(包括革命文物文化单位)在面对红色文化IP转换时,不得不求稳求慎,因而整体开发相对滞后。
相比之下,红色工业遗产在实现IP转换时,显然比革命文物转圜的空间要大得多。因为红色工业遗产如果不实现IP转换,那结局多半只有拆除一途。从实现方式来看,红色工业遗产的IP转换更多是IP赋能,即将自身的媒介记忆转换为IP,再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场景再造,从而提升其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功能,这正是由红色工业遗产的创新性所决定的。
例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是红色工业遗产重镇,在“一五”时期,党中央在平房区建起哈飞、东安、东轻三大国家级军工龙头企业,与“哈军工”形成“一校三厂”的军工重镇。近年来,平房区利用自身资源,打造“红色工业研学”特色旅游的区域游新模式,将现有红色工业遗产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旧址”作为旅游线路合并开发,实现了“东北抗联精神”与“工匠精神”的对接,为红色工业遗产实现IP赋能,从而提升了整个区域文旅产业的价值与当地红色工业遗产的影响力。
“精神谱系+红色文创”是红色工业遗产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路径,IP赋能使之产生了具有创新性与活力的创新价值,但这也对红色工业遗产本体周边的环境状况提出了较高要求。
(三)“精神谱系+地域文化”:基于人民性的社区参与
前文所述红色工业遗产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两条路径,都是基于访客机理。但就目前红色工业遗产的现状来看,大量遗产所在地属于曾经的大型国有企业社区,部分社区人口密度大、总体收入较低、生活环境较差,当中居民多为过去退休老职工及其家属等原住居民及少部分外来低收入租户。调研发现,目前分布于全国各地的红色工业遗产,不少附着于这样的大型社区之上。部分建筑物与构筑物已经成为社区的一部分,形成了规模极其庞大的记忆场所。虽然当中一些社区以腾退、拆迁等形式实现了用地更新,但大多数社区因改造难度大、重建成本高,且已经与城市融为一体(如宜昌葛洲坝社区、鞍山鞍钢社区等),维持现状反而是最好的结果。而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密切相关的企业文化,也已经成为地域文化的一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工作,也必须依赖于社区参与才能实现,而这也成为红色工业遗产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渠道。简而言之,就是“精神谱系+地域文化”的在地扎根传播。此处所言之社区参与,指的是在不改变社区现有居民结构、文化场景的情况下,立足地域文化积淀,挖掘利用“乡愁”资源,将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主体由政府或机构转变为社区居民,以建设“人民城市”为抓手,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有效传播。
例如,红旗渠是新中国水利工程的代表,该工程以“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的气概功彪史册,是新中国水利事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写照,“红旗渠精神”一直被看作新中国水利工作者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这一大无畏品格的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工作者长期甘于奉献,四海为家,全国各地形成了数以千计的大型水利企业社区,留下不计其数的建筑物与构筑物,这是非常独特的红色工业遗产类型。其中以人口最为庞大的宜昌葛洲坝社区最为典型,它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拥有数十万葛洲坝集团老职工。近年来,该集团总部搬迁至武汉并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合并,留下了规模庞大的“后方基地”。搬迁之前,葛洲坝集团与宜昌市西陵区政府合作,在移交物业的同时,依托该集团下属文旅公司、园林公司等二级企业,以国家工业遗产葛洲坝船闸为中心,保护修缮城区内数百处老建筑与构筑物,重塑街区园林绿化,新修葛洲坝公园沿江栈道,新建体现企业发展历程的景观广场与文化墙,保留并丰富了媒介记忆,成功地实现了历史场景再造,并通过维护与建构既有的记忆场所,推动“精神谱系+地域文化”的在地扎根传播。
不言而喻,这一传播路径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植于群众的人民性。当红色工业遗产被处理为记忆场所时,它具有地理物质性与空间物质性双重属性,这一空间是建构在具体人地关系之上的客观实在,不可能脱离对具体人地关系的关注。就此而言,探讨其传播路径尤其应当重视人地关系,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产生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