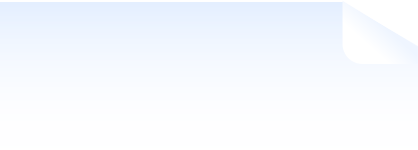数字科技、制造业新形态与全球产业链格局重塑
摘 要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数字经济是其中创新最活跃、增长最迅猛的领域。数字科技的成熟、应用、扩散与融合,推动制造业在产品形态、生产方式、客户关系等方面发生深刻的改变。随着制造业形态的变化,产业链价值链各环节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从单一供给侧条件转向更加多元化,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格局也随之改变。中国应抓住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的机遇,发挥数字经济发达、制造体系完善的优势,完善数字化发展环境、支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重构顾客价值链等,以进一步增强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高在全球分工地位和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掌控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由技术群所推动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中,创新最活跃、增长最迅猛的要数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智能机器人、3D打印、扩展现实等数字科技正在推动制造业形态发生深刻变革,并与逆全球化、疫情冲击推动下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趋势一起,共同影响和改变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地理空间布局。
在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的产品形态、生产方式、客户关系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产品形态从以物质产品和硬件为主转变为数字内容和服务占较大比重;生产方式从工序分工到企业专业化、从“知行分离”到“知行合一”、从大规模生产到定制化生产;客户关系从多层级销售转向平台中心辐射、从信息单向流动转向双向互动、从用户隔离转向用户社群化。
产品形态
1.从物质到数字
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制造业被定义为对采掘品和农产品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物质生产部门。在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的产出主要是以原子、分子形态存在的物质产品,投入也以物质形态的投入品为主。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许多制造业的产出从物质产品形态转变为以比特呈现的数字形态。这一转变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一是物质产品直接以数字化的形态呈现,如图书、杂志、报纸从以纸张为载体转变为完全以数字化形态呈现。二是物质产品生产过程的分解,从产品设计方案到最终产品制造完成的价值链中,产品设计方案、产品原型以数字化形态呈现,最终产出仍是物质形态。在投入方面,除了传统的物质形态投入品外,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和价值的重要来源。
2.从硬件到软件
在工业时代,产品是由各种物质要素及其组合构成的,有着可见的产品架构、物理结构和物质形态。在计算机产业,硬件主要指计算机主机、显示器以及打印机等各种外部设备。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软件在产品中的应用日益普遍、作用不断增强、价值含量占比不断提高。软件是指一系列按照一定规则组织在一起,并能够完成特定功能的代码集合。软件所反映的是人类对现实世界规律的认识,它把人类知识代码化,并自动对各种信号输入按照这些预设的知识作出响应。软件通过发挥定义产品功能强化了硬件的功能,即通过运算支撑硬件完成特定功能的操作;软件还兼具优化产品功能,即软件可以实现原本由硬件实现的功能,但效率更高、结果更优或成本更低。软件日益成为产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硬件一起组合成为完整的产品。无论是机器设备还是消费品,都可以包含嵌入式软件,或通过网络调用云端由更强大的硬件设备、更复杂的代码所提供的计算能力。
3.从产品到服务
在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的产出是产品,制造企业主要从事产品的开发设计和生产制造,并通过一次性销售产品获得收入。制造与服务处于比较独立的状态,制造业与服务业有着较为清晰的边界。但对于大多数产品而言,用户购买产品不是需要产品本身,而是需要产品的使用价值即产品能为用户带来的效应。比如,用户购买电钻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电钻这一产品,而是为了使用电钻打出需要的孔洞。因此,从用户的角度看,企业是提供产品还是服务几乎是无差别的。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产品复杂程度的持续提高,用户或因无法掌握产品的知识,或者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对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从制造企业的角度,也需要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和收入来源。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制造业就开始了服务化转型,制造企业从主要从事生产活动转向更多地提供基于产品的增值服务,从原来主要提供产品转向提供“产品 服务”的组合,从一次性销售产品获得收入转向持续提供服务获得收入。数字科技的发展加强了生产链、价值链中的数据流动和循环,进一步拓展了服务型制造的空间、丰富了服务型制造的模式。
生成方式
1.从工序分工到企业专业化
在工业革命早期,工业产品的结构比较简单,在一家工厂就可以完成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工厂会通过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但主要是工序分工,即不同的工人专业化地从事某个固定工序的生产。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高度垂直一体化的现代工业企业在美国出现并成为美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在泰勒等“科学管理”理论的推动下,生产工序被分解为简单劳动,工人几乎像机器人一样按要求做出重复性的动作,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发生了异化;另一方面,现代企业是对作为投入品的多种产品生产的整合,在其内部存在着车间、工厂层面的分工。科斯等制度经济学学者认为,企业间的分工或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企业对市场交易成本和内部管理成本的权衡。数字科技的发展不断推动交易成本降低,而交通技术的发展又拓宽了市场的范围,使规模经济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来,因此聚焦于自己的核心资源和能力进行专业化经营,而将关联度不大的业务剥离或外包出去成为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多企业的选择。在发达国家,许多知名的大企业频频进行业务剥离和“瘦身”,以聚焦核心能力、发挥专业化优势。
2.从“知行分离”到“知行合一”
这里借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表述,但内涵不同。“知”是指生产经营中的知识与信息;“行”是指生产制造活动。在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企业根据已有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以及生产产品的技术特征搭建生产线。生产线的运转以及所生产产品的调整,通常由工人根据自己的经验人工操控设备,或者由工程技术人员对生产线使用的设备、设备参数、加工模具等进行调整。关于行业生产的知识外在化于生产线操作者的头脑中。在数字经济时代,“软件定义”在制造业中普遍存在,企业在产品制造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知识、技术通过算法和代码内嵌到生产系统之中,软件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对生产设备自动地进行适应性调整,实现知识的复用。在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支持下,对生产线的调整可不依赖现场的工作人员,而是依靠云端的算力、算法和数据对生产线进行控制。
3.从大规模生产到定制化生产
英国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采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原本由手工(以及简单的生产工具)完成的生产活动被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取代,生产的规模大幅度提高,人类社会从早期的定制化生产进入规模化生产时代。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电力随时可用的特征使得大量企业获得了高效率的动力来源,生产力水平得到再一次跃升。连续生产流程的发明、零部件的标准化与可互换部件的普遍采用,使工业生产进入大规模时代,并以福特汽车所采用的“福特制”而著称。铁路、远洋货轮、飞机、集装箱等航运设备、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市场的范围,使大规模生产的产品能够找到市场需求、实现其经济价值,成为工业经济时代全球企业普遍追求的模式。在数字经济时代,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增材制造等技术的成熟和应用,使得生产线的柔性化程度显著提高,即能够根据细分市场需求进行小批量生产甚至进行单件定制,而生产成本不会有明显的提高。
客户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