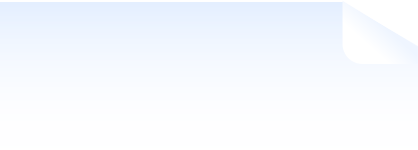以经济理性主义来看待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可以把它理解为“全球一盘棋”——资本、人员、科学技术等可以在“棋盘”上不受阻碍地流动。然而近几年,这盘“棋局”却频生变局——原有的全球产业链被逐渐打破,加速重构。
在黄群慧看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重大因素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并给未来产业链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
第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全球化遭遇到强势逆流,此次“十四五”规划在谈全球化问题的时候重点指出了这个变化。“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变化趋势尤其明显,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加之2020年以来的疫情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来势凶猛,全球化遭遇了强势的逆流。”黄群慧如是分析。
记者观察到,当前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全球出口占全球GDP比例开始下降,主要是出口部分在降;与此同时,像是美国也在提升关税税率,筑高贸易壁垒。
黄群慧指出,这导致我们原来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形成的全球化生产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全球化生产分工开始“内化”,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的巨大风险。
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在发生变化——大国之间围绕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进行博弈,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力量开始崛起,“东升西降”令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黄群慧表示:“在全球宏观经济治理大变局下,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治理框架都面临着巨大挑战,种种基于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博弈都在迫使全球产业链重构。比如说WTO开始面临一系列严峻变革;美国提议为跨国企业设定最低15%的税率;以及美国基于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对中国产业进行打压。”
第三个因素就是科技与产业加速创新的新格局。以新冠疫情为例,2020年年初开始全球大暴发的新冠疫情实际上加速了全球产业与科技的变革。
“疫情之下,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加速迭代。我们在商务办公领域、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生产制造领域以及政府和社区治理领域迎来一系列重大的变革。这也会导致全球产业链布局发生新的变化。”黄群慧表示。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碳中和”与“碳达峰”——这是全球共同采取行动直面挑战、加深国际合作的重要领域,对于产业技术革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黄群慧看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实际上是承担了巨大压力的。据了解,2019年我国碳排放总量大约是98亿吨,占全球大概三分之一,但我们人口只占全球五分之一,GDP只占全球17%点多。
他指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我们只有30年的时间。而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过去一般都经历了50~8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碳减排曲线只会更加陡峭——这对我们的产业链变革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记者了解到,就目前中国产业链现状来看,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在2010年之后就是全球第一。到2016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已经是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的美国、德国、日本的三者之和。
在黄群慧看来,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了,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并未把握关键的核心价值链,尤其是我们产业基础短板明显。“我们关键的核心零部件、关键的基础材料、先进的基础工业、行业的技术基础,这些被称作‘工业四基’的领域,加起来有大概682项短板亟待攻克。”
“事实上,我们常常讲芯片技术不行,或者某某技术不行,折射出的是整个产业基础都存在着短板。”黄群慧表示。
无疑,基于目前这种“大而不强”的产业链基本布局,中国需要重新构建产业链的新发展格局。黄群慧表示:“构建产业链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要基于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大幅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这是最核心的。”
在黄群慧看来,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直接关系到经济现代化体系的建立。那么,未来五年我国应如何统筹推进锻造长板、补齐短板?
首先是构建有利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产业创新生态。黄群慧指出,上述“工业四基”问题的核心就是科技创新能力弱——这是我们产业链革新、经济转型升级的短板所在。而创新不仅仅是一个经费投入的问题,这涉及到完善整个创新生态。
他强调,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努力完善试验验证、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信息服务等基础服务体系;构建产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协同性,构建全社会范围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